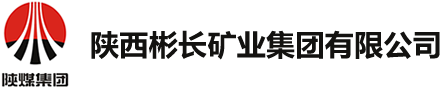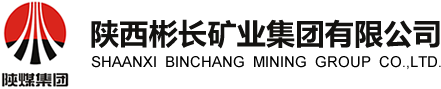文艺生活
黄土高原的褶皱里藏着历史的年轮,路遥用钢笔尖撬开这些沟壑时,渗出的不是墨汁,而是混杂着煤灰与麦芒的生命原浆。《平凡的世界》里没有英雄史诗的鎏金封面,却在锄头与钢钎碰撞的火星中,锻造出一部属于普通人的青铜编年史。

孙少安的胶鞋永远沾着双水村的泥,这抔黄土里拌着祖辈的骨灰与弟弟的远方。开砖窑的火光中,我看见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迁徙的剪影。他数砖坯时的神情,与父亲孙玉厚拨算工分时如出一辙,只是算盘珠子上凝结的汗碱,变成了砖缝里渗出的现代化阵痛。这个被土地拴住双脚的汉子,在砖窑腾起的黑烟里,完成了中国农民最悲壮的转身——既要对抗饥饿年代的生存法则,又要迎接改革春风的凛冽。
金波的马头琴声在青海草原被风吹散时,我听见了工业化浪潮吞没游牧文明的呜咽。这个用军用水壶装烈酒的青年,把失恋的苦楚酿成了信天游,却在装满瓷砖的卡车轰鸣中哑了嗓子。当他最终成为穿西装的包工头,那些曾经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爱情,都变成了混凝土里的钢筋骨架。
与哥哥相比,孙少平的世界更为辽阔。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走进县立中学那日,西北风正卷着1975年的政治标语呼啸而过。他蹲在墙角吞咽高粱面馍的模样,像极了那个时代所有蜷缩的青春。食堂泔水桶里漂浮的菜叶,宿舍床铺下潮虫啃噬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这些细碎如尘的日常里,却蛰伏着觉醒的闪电。当他在破败的县图书馆翻开《红与黑》,于连的野心与黄土高原的苍凉在书页间轰然对撞——知识这柄双刃剑,既劈开了蒙昧的茧房,也划开了理想与现实的鸿沟。
三十年后重读这部百万字巨著,突然在孙兰香考入大学的段落里触摸到路遥的温柔伏笔。这个躲在磨坊写作业的小姑娘,后来戴着校徽走进校园的身影,何尝不是穿过了父兄用血汗浇铸的桥梁?那些被生活反复揉搓的人们,在皱纹里刻下的不是沧桑的年轮,而是通往星空的等高线。
合上书页时,工地上打桩机的轰鸣正震颤着城市的地基。恍惚间看见无数个孙少平从玻璃幕墙的倒影中走来,他们安全帽下的眼睛依然亮着煤油灯般的光。这部写于三十年前的作品,至今仍在为我们这个急速膨胀的时代把脉——当物质的沙尘暴迷了双眼,唯有那些在平凡中坚持仰望的人,才能在掌心养出不会干涸的月亮湾。(救援中心 孟枭)
编辑:达文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