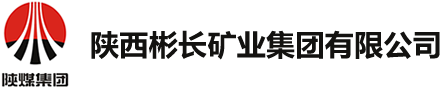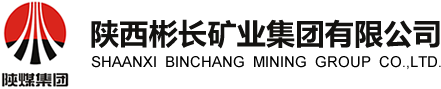文艺生活
看完《南京照相馆》走出影院时,夏日的阳光刺得我眼睛生疼。影院外车水马龙,美食街上的叫卖声此起彼伏,可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,是暗房里的那盆显影液。当日军屠城的照片在药水中慢慢浮现,阿昌颤抖的手让镊子掉进盆里,"叮"的一声脆响,仿佛砸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。
银幕上的“南京照相馆”其实是座暗房,刘昊然饰演的邮差阿昌第一次摸到相纸时,手指抖得像秋风里的梧桐树叶。他冒充学徒给日军冲洗底片,显影液里浮现出来的却是砍头、活埋、江边堆积成山的尸体。有个镜头让我不自觉攥紧了座椅扶手,阿昌举着底片贴在墙上,光影里南京城的轮廓突然扭曲,变成了他怀里那封没送出去的家书。王骁饰演的老金蹲在地下室,用指甲在青砖上刻下“耻”字,灰尘簌簌地落在他女儿的虎头鞋上,那孩子还不知道,自己的摇篮曲里,正夹杂着远处的枪声。
高叶饰演的毓秀把罪证底片缝进戏服里时,旗袍上的牡丹花纹被鲜血浸透,却一边对着镜子描眉,一边说:“唱了半辈子穆桂英,总得在戏文里活一回。”最戳人的还是老金举着相机冲向日军的场景,老金的白发沾着干涸了的鲜血,却把镜头对准侵略者:“老子就是拍照片的!”快门声和枪声重叠的一刹那,我突然看清他胸前的怀表,玻璃早碎了,时间永远定格在了1937年12月13日。
电影散场后,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,影片中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,就像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玻璃柜里的钢笔,笔尖还凝着墨,却再也写不出下一行字;就像展台里的破布鞋,鞋跟磨穿了,可鞋尖朝着的方向,永远是回家的路。这些老物件哪是物件啊,是无数双没闭上的眼睛,在问我们:“还记得吗?”
记得什么呢?记得1931年9月18日夜里的炮声,震碎了多少家庭的窗;记得南京城墙上的弹孔,至今还嵌着生锈的弹片;记得731部队实验室的铁架,冷得像冰,却烫过无数滚烫的生命。有人说“都过去了”,可那些在黑夜里举过的拳头、在废墟里埋过的希望、在最后一刻还想着“要留下点什么”的人,他们没说“过去了”。
几年前去哈尔滨,看到一位白发老人在731遗址前颤巍巍的鞠躬。他说父亲当年是抗联战士,连张照片都没留下,我来替他看看,这罪证还在,就好。那一刻我突然明白,我们去纪念馆,去看那些沉重的展览,是在替那些没能走到今天的人,好好看看这太平盛世;替那个藏底片的师傅,看看如今的照相馆里,全家福笑得比阳光都暖。
有人问铭记历史是为了什么?是为了守护那些在黑暗中熄灭的无数条生命;是为了不忘来时路,不走回头路,勇往直前;是为了前方的万家灯火、点点繁星,这正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努力的意义所在!
1937年冬,南京城破,三十万手无寸铁的百姓倒在血泊中。他们不是冰冷的数字,是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,是灯下缝补衣裳的老者,是为生计奔波的商贩。那些幸存者的血泪控诉、累累白骨的无声呐喊,时刻提醒着我们,这段悲惨历史,绝不能忘,也不敢忘。
当记忆被刻意抹去,暴行便可能重演。铭记不是为了延续仇恨,而是要让后代看见,文明的底线如何被践踏,人性的光辉如何在绝望中闪烁,那些冒死保护无辜百姓的国际友人,那些在废墟中传递食物的双手,那些用日记记录真相的眼睛。历史是面镜子,照见过去,也映出未来。我们背负着三十万个名字前行,不是为了沉溺于伤痛,而是要在和平年代守护好每一个平凡的清晨与黄昏,让“永不遗忘”成为对生命最庄严的承诺。(铁运分公司 付媛媛)
编辑:达文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