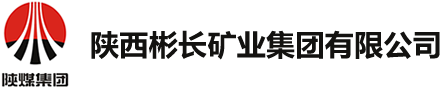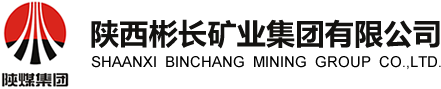文艺生活
前几天休假回了趟老家,最大的感触是酸枣长疯了。
一进入山间便被漫山的红震住了。此时,正是酸枣果红透的季节,那灼灼的红,从一家家窑洞崖脸延烧到一片片山坡上去,轰轰烈烈,一路摧枯拉朽烧着了整座山。
酸枣从不是讨喜的模样,没有高大的枝干,也没有舒展的冠幅,常以低矮灌木的姿态蜷在荒山陡坡上,满身尖刺透着“不好惹”的劲儿。它的花是黄绿色,小小的一簇簇挤在枝桠间,淡香似有似无。可成熟的果子却像一串串红玛瑙,裹着薄而韧的皮,酸得人直眯眼。
小时候,我总觉得酸枣是农人的“死对头”。
春天耕种时,父亲扶着犁走在前头,我攥着镢头跟在后面,既要把犁断的酸枣根须扔到路边,还得把没断的连根刨出。看似细弱的苗子,根却扎得又深又顽固。我累了就拦腰斩断。父亲见了便说:“根不除净,过几天又冒头!”果然,庄稼苗刚探出土,酸枣已蹿得半尺高,父亲只好再清除一遍。
夏天放羊时,羊群总爱围着酸枣丛啃叶子,腿常被尖刺划出一道道血痕,更怕的是酸枣枝里藏着蜂窝,羊若惊了蜂群,便会甩着头乱蹿,我也常跟着遭殃,被蜂蜇得满头包。这时爷爷会折根细草秆,从烟锅杆里粘出烟油抹在包上,又疼又呛,至今想起还让我皱眉头。
秋天收获时,酸枣经常藏在豆杆里,冷不丁就抓一手刺,疼得连声咒骂。架子车更怕它,轮胎常被扎漏气,父亲脾气急,轮胎一漏便会烦躁地踹车。半夜补胎时,母亲蹲在边上帮忙,补得多了竟无师自通。父亲外出打工后,她就亲自上手,技艺精湛,连村里的老爷们都来请教。我上学时自行车被扎,自己尝试无果,最后还得母亲出手。
冬天劈柴时,酸枣最是棘手,枝干细却硬,满身尖刺,劈的时候不仅费劲还易被扎到,劈好的柴也只能乱堆在旁。拿的时候得捏着枝梢小心翼翼,往灶膛里添柴的时候,也得时时提防。母亲眼神不好,手上常扎进小刺,每次都喊我帮忙。我也被扎过,两人凑在灯下,她捏紧我手上的皮肉,拿针头一点点挑,疼得我龇牙咧嘴。
就连行道的草丛、窑洞的崖脸、山地的塄坎等等,隔上两三年就得清理一遍。祖祖辈辈跟它“斗”了不知多少年,才勉强将它赶上了荒山陡坡、悬崖峭壁。可短短十几年,村里人气渐少,它倒得了势,星星点点的苗竟燎原成了漫山遍野的红。
其实酸枣也不全是坏处。那会儿村里大多用酸枣枝编篱笆门,母亲会挑刺最密的枝条,编好的门满是尖刺,防盗又结实。我多次忘带钥匙,想翻进去,看着密密麻麻的刺,终究都望而却步了。有些长势好的酸枣,会被嫁接成枣树,结的枣小巧玲珑,酸甜可口。
爷爷最钟爱酸枣醋。每年酸枣果红透,他就忙着摘枣、清洗、晾晒,然后装进大瓮里,加水、密封、发酵……等醋酿好,他会接满一小壶,像喝酒似的酌起来。若有人路过,他便热情地喊来品尝,要是对方夸一句“这醋够味”,他还会再送一瓶。我曾好奇地尝过一口,那酸味直冲天灵盖,感觉牙齿都像要被酸掉了。
《神农本草经》把酸枣果列为上品,说能“安五脏,轻身延年”;《名医别录》也说它“补中益肝,坚筋骨”。如今城里人压力大,酸枣仁能安神助眠,价格涨了不少,倒成了村里老人的生计来源。谁家山上的酸枣就归谁,有时还会因为争一片酸枣丛闹别扭。谁能想到,昔日人人嫌的“害草”,如今成了宝贝?
这么多年,从不是我们“斗”赢了酸枣,而是它一直就守在这里。在悬崖上,在荒坡间,遗世独立地看着村里的人来人往,看着岁月变迁、历史更迭,看着我们从嫌弃它、提防它,到珍视它、依赖它。它的刺,早已扎进了这片土地的过往里,扎进了秦皇汉武的传说里,也扎进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日子里。(小庄矿 计忠荣)
编辑:达文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