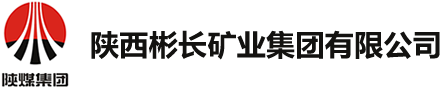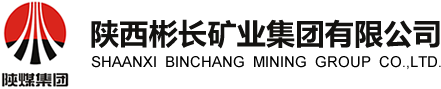文艺生活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,腊八粥,喝几天,哩哩啦啦二十三……”孩子跟着点读书哼唱的童谣,像一把旧钥匙,轻轻开启了岁月深处那扇藏着往昔的门,我的心也随之飘进了旧时光的庭院之中。
我生于农历小年,那时家中经济拮据,生日时没有造型精美的蛋糕,一碗热气腾腾的红糖荷包蛋,加上母亲包的萝卜馅饺子,却也吃得心满意足。或许正因如此,过年于我而言,总有种难以言表的眷恋之情,那是对家的深深牵挂,对亲情的浓浓依恋,对传统节日的执着守望。
犹记得儿时,大抵从五六年级起,身为家中长女的我便主动承担起部分家务,早早体会到了父母持家的艰辛。祖父母在世时,每逢岁末年初,家里总是格外忙碌,过年仪式感十足。父母的身影穿梭于家中的每一个角落,为了这个家的温馨与团圆默默付出着。
腊月二十三过后,大扫除的序幕正式拉开。全家老小齐上阵,我和弟弟小心翼翼地将屋内物件逐一搬到院子,母亲用干净的湿布仔细地擦拭着那岁月留下的尘埃,那些家具在母亲的手中渐渐焕发出原本的光彩。父亲给扫帚绑上长长的杆子,裹着头巾,将屋顶和角落里堆积的灰尘清扫干净,一时间,屋内尘土飞扬,却也充满了别样的生机。祖父母也没歇着,祖父戴上老花镜,提着工具箱,一件一件地查看那些旧家具,仔细地修修补补,让它们不光能用,还多了些往日的温情。祖母坐在院子里,手上忙着用针线缝缝补补家里的旧衣裳。每一件衣服都藏着家里的故事,经过她的手,就像又活了过来。物件归位后,母亲和我又忙着揉面蒸馍,有招待客人的普通馍,有寓意吉祥的拜年花馍,还有初一要吃的馄饨馍,馍里包着硬币、辣椒、麦麸、葱油,藏着对新年的祝福与期许。我还兴致勃勃地跟着母亲捏果子,花朵形、圆形、菱形,甜咸交织,随后一起烧油锅,炸果子、虾片、丸子、豆腐干、花生米,灶房里弥漫着诱人的香气。父亲则挑起采买年货的重担,水果、干果、蔬菜、肉类……将袋子塞得满满当当。回来后便忙着杀鸡宰鱼、准备熟食,烟火升腾而起,香气弥漫在整个院子,满是年的味道。
有一年,母亲闹出了个乌龙,她做的肉碗扣过来的肉片竟然是反的,全家人先是一阵惊愕,随后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,这成为那年春节独特而难忘的记忆。
除夕夜,我和弟弟满心期待着父亲煮好的喷香的肉,能啃上剔剩的肉骨头,那是属于我们孩子们的简单快乐。母亲在一旁准备着初一包饺子的馅料,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守岁,电视上春晚的欢声笑语与外面鞭炮的噼里啪啦相互交织,暖黄的灯光洒下,温馨满溢。
过了大年初一,前来拜年的亲戚络绎不绝,父亲化身为大厨,烹饪出满桌的美味佳肴,凉菜热菜、鸡鱼虾、甜盘子、肉碗碗……应有尽有。客人太多时,便分桌而坐,男桌、女桌和小孩桌,大人畅谈家常,小孩拿着压岁钱嬉笑玩闹,宛如一场热闹的家宴。我穿梭其中,热情招待,大家对我称赞有加,夸我成绩优秀又懂事勤快。那时的我,也曾对父母安排的活儿有过怨言,但如今想来,皆是温暖,那些曾经的忙碌与琐碎,都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。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,过了腊八就是年……”童谣声中,往昔的岁月渐渐远去,尽管年的模样已变,但童谣里的温暖与欢乐,如陈酿,在岁月里愈发香醇,成为我记忆中永不褪色的珍藏。(贾亚茹)
编辑:达文娟